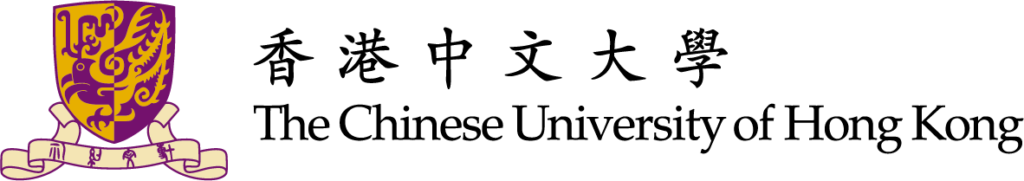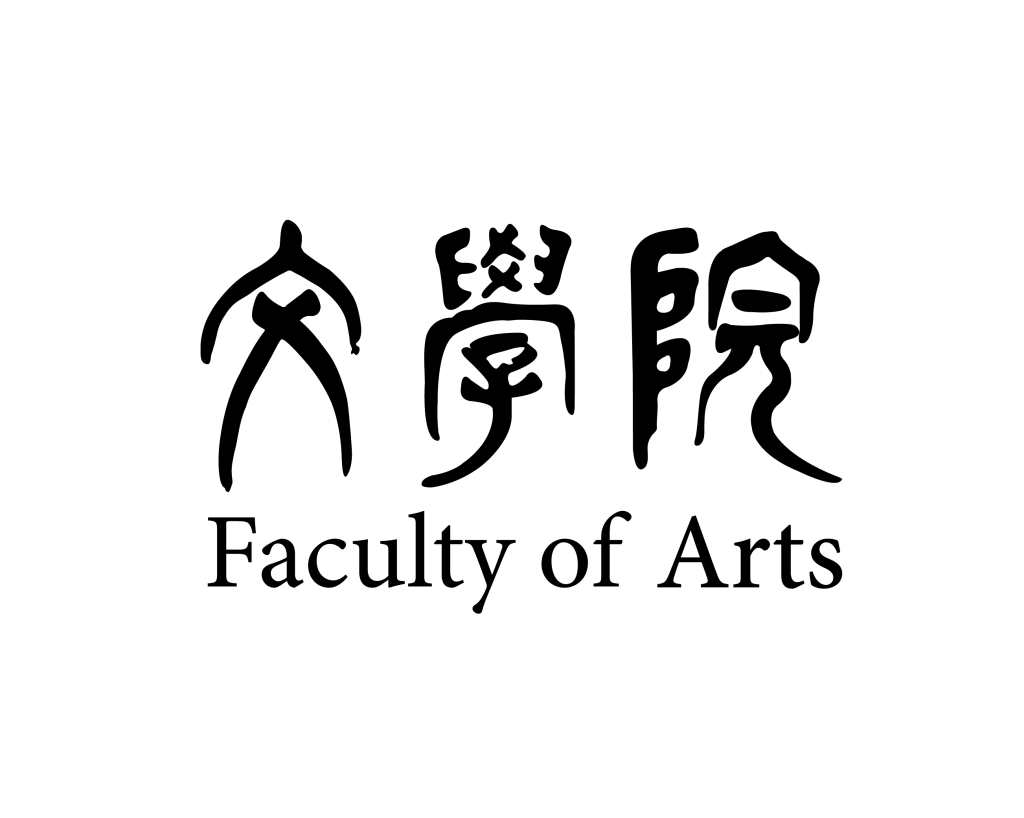【2020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重寫冷戰時期電影史:琪拉.穆拉托娃和她的電影
文// 譚佳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2020年了。俄國人仍然是主流荷里活電影中毀滅世界虐待女性的邪惡擔當。例如《天能》(Tenet),也許是為回應近年對於全白人卡司的批評,難得由黑人擔任男主角,但依舊演繹着美國男性拯救世界、拯救(白人)女性的劇本。這種長期以來充斥在動作片間諜片科幻片中的性別以及冷戰想像,在今天這個疫情下全球經濟開始脫鈎( decoupling)的時代卻不見退潮,依然如故。因此,當我看到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是導演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時,不由得眼前一亮。
VGIK與奧德薩:蘇維埃蒙太奇與蘇聯時期的穆拉托娃
常見的對穆拉托娃(1934–2018)的介紹會說她是著名的烏克蘭女導演,我們也許會想當然地以為她是烏克蘭裔,拍攝講烏克蘭語的電影。但穆拉托娃並非烏克蘭裔,她的絕大部份電影是用俄語拍攝。她的一生都被冷戰的地緣政治形塑,將其前大半生形容為蘇聯導演更為準確。穆拉托娃出生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當時是羅馬尼亞(Romania)的一部份,還不屬於蘇聯。她的父親是俄羅斯人,在她小時候就死於戰爭。她的母親是羅馬尼亞官員,羅馬尼亞變成蘇聯一部份後在政府任職。穆拉托娃曾在位於莫斯科的國家電影學院VGIK學習,學校的全名是All-Union 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是蘇聯時期以及當代俄羅斯最有名的電影學院。[1] VGIK創立於1919年,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電影學院。當年的開創者有庫里肖夫(Lev Kuleshov),著名的電影剪輯術語「庫里肖夫效應」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許多蘇維埃蒙太奇學派的領軍人物都曾是VGIK的老師,包括愛森斯坦。穆拉托娃的本名叫Kira Korotkova ,她在VGIK 讀書的時候與烏克蘭人亞歷山大.穆拉托夫Alexander Muratov 結婚並改從夫姓。改從夫姓在當時的蘇聯女性中非常少見,不知是否與她在VGIK畢業之後去了烏克蘭的奧德薩工作有關。
稍微熟悉電影歷史的人都知道,「奧德薩階梯」是1925年蘇聯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中的經典片段,現在仍然是闡釋蘇維埃蒙太奇(Soviet Montage)理論的不二之選。電影中描繪了沙皇屠殺平民而激發了戰艦軍人的起義的過程,但曾經是蘇聯的一部份的城市奧德薩,現在已是烏克蘭的重要港口城市。雖然奧德薩在烏克蘭,奧德薩這個名字卻和蘇維埃蒙太奇學派息息相關。同時,奧德薩電影製片場也是蘇聯時期重要的國有製片廠。雖然蘇聯解體之後穆拉托娃成為了烏克蘭的公民,但她並非烏克蘭裔,也只任職於蘇聯時期的奧德薩電影製片場。穆拉托娃早年所受的教育和創作,體現了蘇聯時期的電影教育與製作的集中化特點。她與2014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焦點影人瑪特.美莎露絲( Márta Mészáros)頗有淵源。美莎露絲生於1931年 ,據說是東歐匈牙利歷史上第一位女導演。兩人都曾於蘇聯時期在VGIK學習。美莎露絲在1956年畢業,是1959年畢業的穆拉托娃的學姊。[2]
電影史的冷戰化:被遺忘的電影史中的蘇聯與女性
筆者有幸在幾年前受邀參加VGIK電影節,感受了歷史的沉澱。也順便去愛森斯坦的墓前憑弔,還參觀了不再輝煌的莫斯科電影製片廠。VGIK的教學樓前屹立着一個以傳記《雕刻時光》聞名的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雕像,他也是VGIK最有名的校友之一。面對塔可夫斯基我不禁有些唏噓,電影的書寫,存在許多斷層。英語電影歷史書寫的西方中心主義大家大概都有所了解,華語電影的研究也是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在海外收到關注之後才開始有顯著的發展,對香港台灣新浪潮的研究興趣和著作才開始增加。冷戰時期華語電影普遍被忽略,近年才略有改善。
蘇聯電影和亞非拉電影的歷史書寫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早期蘇聯電影對西方電影有很大影響,和冷戰時期的隔閡對比強烈。這種電影史的冷戰化在英語書寫的電影史以及美國的電影教育中甚為明顯。早期蘇維埃電影人例如以愛森斯坦為代表的蒙太奇理論和維托夫(Dziga Vertov)的電影眼(Kino-eye)理論都有很重要的位置,更是世界電影史的必教內容。但冷戰開始之後的蘇聯電影歷史大都被邊緣化,更遑論蘇聯時期的女性影人。穆拉托娃的電影也要等到1988年才在法國著名的Créteil女性電影節上有回顧展,從那開始她的電影才被更多英語世界的藝術電影愛好者知曉。重新回顧她的電影,有着從蘇聯時期電影和女性影人的角度重寫電影歷史的雙重意義。
蘇聯精英女性的哈姆雷特式處境:「洗碗還是不洗碗,這是一個問題。」
《萍水相逢》(Brief Encounters,1967)是穆拉托娃第一部導演的作品。電影的開場是在一個舊式房子的廚房裡,鏡頭清楚交代了廚具與環境。正當我疑惑作品是否會在借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時,女人自言自語,問出了哈姆雷特式的對於家務的質疑:洗碗還是不洗碗,這是一個問題。原來她正面對着堆積如山的碟碟碗碗,邊寫邊練即將參加的農業會議的發言稿。這場戲的一些主題貫穿了穆拉托娃幾十年的電影生涯。首先,穆拉托娃很關注蘇聯時期職業女性精英的處境。這些女主人公都不在一個傳統的核心家庭關係之中。《萍水相逢》的水務處女官員的地理學家愛人長期在外,她在家政工到來之前長期獨居;在穆的第二部電影《漫長的告別》(Long Farewells,1971)裡,中年單身離異母親是一個政府翻譯人員,和兒子住在一起;《衰弱症》(The Asthenic Syndrome,1989)前半部份的主角是一名剛剛喪偶的年長女醫生。蘇聯並不乏女權主義思潮,早期柯倫泰 (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從鼓勵革命與愛情的解放 到國家政策上的保障女性參政以及男女同工同酬,在同時代的世界範圍內都有進步意義。穆拉托娃出身精英家庭,又受過傑出的電影教育,她的影片反映了蘇聯時期精英婦女的地位,可又絕不僅限於此。
以今天的眼光而言,電影以職業女性為主題不是新鮮事,但二戰之後歐美女性從戰時積極參與經濟軍事活動轉變為退居回到家庭中。當時以女性為主要題材的情節劇許多是關於家庭主婦的故事。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的電影大多講述郊區美國理想生活背後的壓抑與苦楚,例如1955年的《深鎖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以及同時期電視情景喜劇《我愛露西》(I Love Lucy,1951–1957)也大受歡迎,都是描述中產家庭主婦的生活。這樣對比之下,穆拉托娃對於非典型家庭的精英女性的探討很有先鋒性。
穆拉托娃的非典型家庭精英女性的題材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卻有另一層意義。社會主義美學之下,精英女性並不是電影裡的常客。筆者與中文世界的大部份電影愛好者相同,對蘇聯時期的電影缺乏了解。因此本文粗略談談早期穆拉托娃與同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電影的一些對比與觀察。穆拉托娃與中國導演謝晉年齡相近,兩人的導演生涯都橫跨近半個世紀,兩人的電影都受政治運動的影響而命運多舛。謝晉也擅長講述女性的故事,1964年的《舞台姐妹》更是經典之作,當時也被禁映。但這些電影大多講述底層婦女的故事以及她們在新社會裡的新位置。在這些故事裡,女性很容易成為某種壓迫之下的受害者,這些壓迫被抽象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女性最終被革命拯救。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女性敘事裡,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勞動婦女與底層婦女,而很少出現精英女性作為主角。即使是謝晉在改革開放後拍的《最後的貴族》裡的貴族小姐也是流亡海外的華人,而不是毛時代的女性精英。
另類情節劇,非線性敘事與視覺隱喻
我把穆拉托娃的電影和歐美家庭主婦電影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群眾婦女的電影做對比的另一個原因,是這幾種不同文化歷史脈絡裡的影片都着重講述女性的生命經驗,形式上也有一些情節劇(melodrama)的特徵。《萍水相逢》是一個三角戀故事,妻子是地方官員,丈夫是需要長期在外進行勘探工作的地理學家。丈夫在外偶遇年輕女子,年輕女子為了追求男子而找到他家,被妻子誤以為是家政工。於是兩個女人同在屋簷下生活。《漫長的告別》主要講述單親母親和十幾歲的兒子的生活瑣碎,以及他們之間時而疏離,時而親密的母子關係。這些影片中的巧合和對戀愛以及家庭關係的關注都是情節劇的主題。連穆拉托娃也認為自己早期的電影是provincial melodrama,在這裡我將它翻譯為另類情節劇。
另類情節劇至少有兩個層面的意思,首先是影片使用了情節劇的一些特徵,但以非主流的方法呈現。雖然主流情節劇容易形式化且煽情,但在藝術電影中,從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到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都擅長在借用情節劇一些特徵的同時,開創出獨特的敘事和視聽語言。穆拉托娃的早期電影亦是如此。在《萍水相逢》兩女一男的故事中,男人只在兩個女性的閃回(flashback)中出現。電影的非線性敘事以及倒敘結構在影片中有着重要位置,而閃回部份更是佔據了影片一半或者更多篇幅。在敘事上,影片的結局是在家政工/情人擺好餐桌之後,選擇了離開,這似乎暗示着第三者的退出,以及原有家庭的復原和穩定。但是非線性的倒敘結構又給文本帶來更多的開放性,因為在兩個女性的萍水相逢裡,男人既是在場也是缺席的。他只存在於兩個女性的主觀回憶裡,直到電影最後的餐桌的空鏡裡也依然沒有出現。這樣的非線形敘事讓故事由兩位女性的情感來推動。在妻子的回憶裡常有她對關係的疑問。而在家政工的回憶裡她對感情和生活的態度勇敢而獨立,其中一個很有名的鏡頭是她和朋友陽光地走在寬廣的馬路上,遠處是矗立的山峰。
另一方面,在蘇聯中央集中體制下的奧德薩製作俄語電影,是地理與文化資本上的雙重邊緣,但這也是她能拍出這些不尋常的電影的原因之一。她把兢兢業業的水務部政府女官員的故事重點放在了她對情感的追求上,也用很多心力呈現「第三者」的感情。《漫長的告別》拍出來之後被審查機構認為屬於「小資產階級」,又因影片開始於墓園而被質疑為甚麼要呈現墓園和死亡。甚至烏克蘭電影委員會的主席也因為允許這部片子的拍攝而被解僱。[3]《漫長的告別》被禁了十六年,但在被禁期間仍會在VGIK內部放映,並被認為是她最成功的電影。[4]
穆拉托娃的早期電影台詞比較多,這也是情節劇的特徵之一。與現在的中國電影審查類似,在蘇聯拍電影需要劇本先通過審查才能獲得國家的資金來拍攝。這也解釋了台詞與畫面的複雜關係。她的能力也體現於與審查部門周旋之中,不管電影能否放映,至少能先拍出來。她早期電影的題材不算驚世駭俗,拍出來之後卻屢屢被禁,很大原因在於她充分發揮電影視覺語言的複雜性。穆拉托娃擅長用長鏡頭中複雜的場面調度和鏡頭語言交代人物關係,也常使用鏡子或其他帶象徵意味的視覺隱喻,如《萍水相逢》的吉他,便是缺席的男人的視覺隱喻。 在《漫長的告別》中,母親偷聽到兒子和前夫的電話,知道兒子想離開她去和父親同住,母親回到家裡翻弄投影機,把家庭照片放映到牆上。當兒子與前夫的照片出現在牆上時,兒子打開了門,照片映到他的身上,於是前夫以一個幻影的形式,出現在母親與兒子之間。除了之前提到的《萍水相逢》的非線性敘事,《漫長的告別》的好幾場戲也用了非線性剪輯,重複同一個片段,或者把兩個相似拍攝角度的片段剪在一起。比如在接近電影尾聲時,重複播放母親在一個頒獎儀式上風光的場面,和重複的現場舞台配樂剪輯在一起,反襯出之後母親慌張尋找兒子時的落寞。這些複雜的運動鏡頭與場面調度、非線性剪輯和使用帶象徵意味的視覺隱喻,在1978的《寬廣的世界》(Getting to Know the Big Wide World)中發展成「裝飾主義」美學。正是因為善用複雜的影像語言,《寬廣的世界》才把劇本中原本表現社會主義蒸蒸日上的工業建設題材拍出了建築工地的荒涼感,甚至帶有末世象徵意義。
審查,動物,與末世
雖然她的電影長期受到審查,但就今天觀眾的眼光來看,有些地方並不見得如何離經叛道,反而在歷史情境中更能理解電影的先鋒性和電影人的能動性。對於蘇聯時期電影被禁的強調,恰恰是冷戰思維的表現,是對於(反)審查本身的迷戀。穆拉托娃在1990年,也就是蘇聯解體時接受參訪時說過的一段話耐人尋味,「我不覺得我們和西方社會有任何根本上的區別。大致而言,人類在哪裡都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個世界上的苦難和殘酷都是超越了理解的存在。」[5]
很少人談及動物在穆拉托娃的電影中的敘事和影像的意義。《萍水相逢》中人和狗的對視承載了情人之間的目光流轉和心情變化。《漫長的告別》裡的狗叼着高跟鞋在海邊玩耍,是中產休閒生活的有機部份。《衰弱症》裡很長的鏡頭注視着關在籠子裡的狗群,牠們的身上臉上滿是蒼蠅,不斷地直視鏡頭。《衰弱症》講述了在莫斯科地鐵上成群的乘客感染上未知的病毒,逐漸虛弱、陷入沉睡的故事,常被理解為蘇聯解體之前衰敗的國族寓言。但也許這種對人類社會的末世想像,夾雜着對動物殘酷處境的呈現,並不僅限於對蘇聯政權的批評,也是對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文明發展的質疑。這種質疑也體現在《寬廣的世界》中建築工地給人帶來的荒涼感。
正如蘇珊.巴克—莫爾斯(Susan Buck-Morss)所言,冷戰的雙方是如此不同,但同時又如此相似,因為兩者都通過大型工業建設來改變自然環境,從而製造樂觀的社會想像。[6] 在人類與新冠病毒共存的今天,我們對穆拉托娃的電影也許可以有新的理解: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人類社會的工業化方式以及對自然的掠奪卻並沒有改變。當疫情之下的社會政治想象不再樂觀,甚至「新」冷戰漸漸逼近,穆拉托娃的電影裡的末世感就成為對當下人類世的啟示。
注釋
[1] Jane Taubman, Kira Muratova, Tauris, 2005.
[2] 更多資訊,見 https://www.bfi.org.uk/news-opinion/sight-sound-magazine/comment/obituaries/kira-muratova-great-fearless-ukrainian-director
[3] Taubman, 23
[4] Taubman, 20.
[5] Taubman, 45.
[6] 見Susan Buck-Morss,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MIT press, 2002.
(原載於2020-10-14 映畫手民 https://www.cinezen.hk/?p=9334&fbclid=IwAR3H0O-KnAoCC8kDaCK4Pg_o0092_cAQZ6aVG10b0__FhOCAkI8yaiArR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