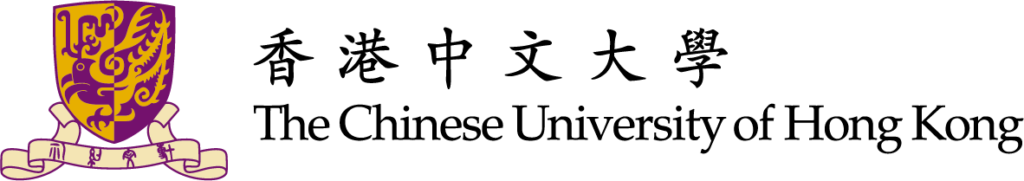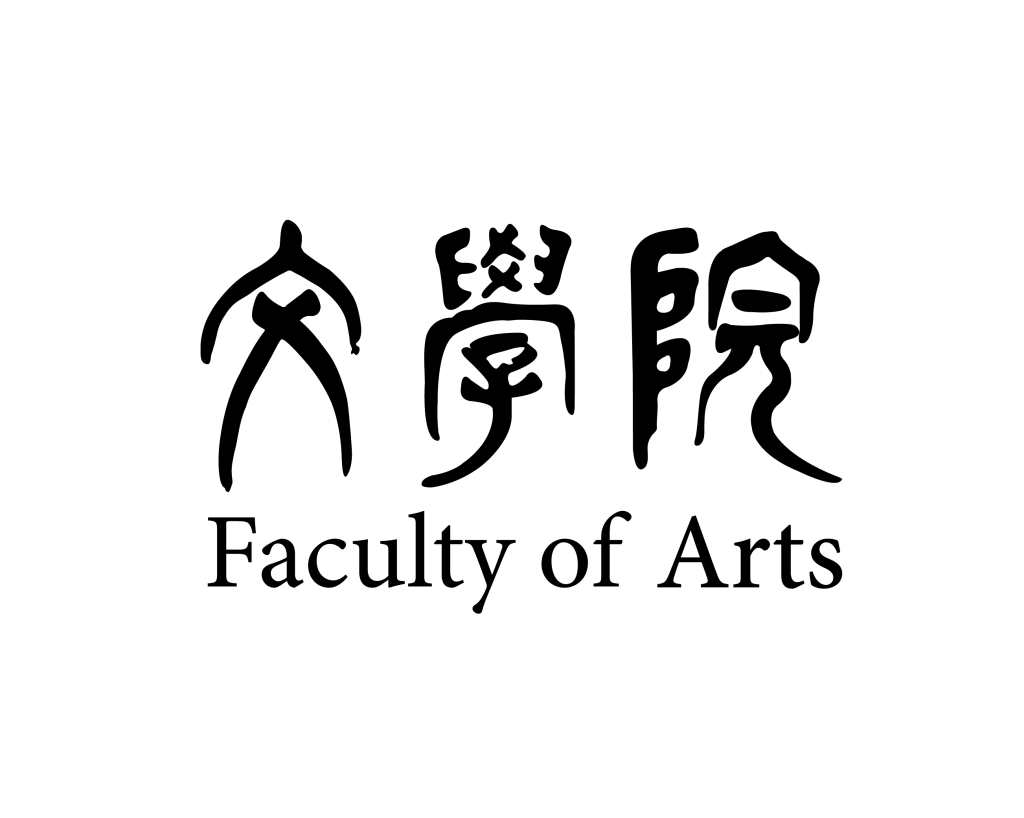香港的時代證言:紀錄集體的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民現》
文// 黃涵榆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當我在六月初從網路社群媒體得知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文後引為《民現》)的出版訊息(原為英文著作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我在知識和情感的層次上都受到頗大的震撼。
雨傘運動在形式上可計算的時間似乎已經結束,但是它所傳達的訊息、激發的追求民主的慾望和動力、對於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衝擊和啟發,都朝向未來開放,是進行中的、是將臨的。
做為一個研究過安那其和佔領運動的學術工作者和關心香港民主抗爭的台灣人,我對於彭麗君教授能有勇氣書寫這樣的一場運動或是尚在進行中的歷史過程感到相當佩服。我等不及台灣通路鋪貨之前,就立刻透過網路向手民主版社訂購這本書,也因此和主編譚以諾結緣,能有機會和讀者們分享一些想法。
《民現》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我其實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將雨傘運動放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全球一連串佔領(或「起義」)行動的脈絡之中,這些行動在起源、動員方式、訴求與目標等面向各具殊異性,共同點在於個體進行集體抗爭,催生政治行動的共同體。
第二部更貼近雨傘運動本身,探討與運動相關社交媒體、藝術創作、紀錄片和影像生產。第三部則回到普遍化的理論高度,從都市權、自由與其規限、法治等角度反思雨傘運動及其後的反逃犯條例(在台灣通稱「反送中」)抗爭。
《民現》在出版登記上的類別「文化研究」、「香港研究」和「政治理論」無法完整呈現其跨文類與學科領域(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藝術、人類學等)、多重文本互涉的特性。
對當代西方理論有所涉獵的讀者應該會與本書頗為契合,作者旁徵博引充分展現對各家理論的熟稔。但本書絕非僅是當代理論大全,而是具有歷史縱深,從殖民到後殖民的歷史軌跡,描繪香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態。
同時,本書透過人類學式的訪談與調查,讓讀者感受到真實人物的生命歷程的親近性。我甚至認為《民現》就是正處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香港的時代證言,記錄傘運及其後的發展,展現一種「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不僅如此,《民現》也嚴肅思考香港的政治出路,大膽地提出重新想像主權的可能性。
作者彭麗君從傘運和任何具有積極意義的抗爭行動看見民眾自我作主的「主權時刻」,跟隨既有的規則,但又參與規則的創新。她相信香港可在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架構下實踐城市自主與民主,在「次民族」的層次上成為民主的實驗場域,讓民主的潛能從單一主權的民族國家的框架中解放出來,實現主權共享或多重主權。
顯然阿蘭特(台灣通譯為「鄂蘭」)的政治哲學是《民現》的思想核心。香港學界也許和台灣學界一樣,一直存在著對於西方高理論的抗拒,一直有(特別是自我標榜為左派的)學者視歐陸理論為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勢力的產物,因而主張「以 XX 為方法」(XX 可為亞洲、東亞、中國、香港或台灣)。
作者彭麗君打開西方與非西方、亞洲與非亞洲之間僵化的、被物化的界線,將阿蘭特的思想遷移到當代香港進行對話。她引述薩伊德(Edward Said)的說法,主張「理論本來就該四處旅行」。
以阿蘭特為響導的理論旅行通過傅柯(Michel Foucaul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巴特勒(Judith Butler)、哈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編織出更豐富多元的文本互涉和思想圖像。我們也在這樣的過程中看見阿蘭特沒有著墨的議題,包括身份認同、私人領域的情感與衝動如何影響政治行動、藝術如何激發政治效應等等,這些都是反思雨傘運動不可迴避的議題。
《民現》的核心概念「現身」(appearing)在阿蘭特的思想體系裡是政治的前提也是宗旨。抗爭運動關乎的是「民眾現身」,那是過程,也是事件,擾亂了日常生活的軌跡,抗拒簡化的因果關係。可以確定的是,參與抗爭運動的民眾不再是抽象的人口概念裡的統計數字,而是受追求民主的欲望驅使、上街頭表達憤怒與不滿、提出政治訴求的能動主體。
雨傘運動的發生和抗爭的香港民眾的現身不外是要求港府特首的「真普選」,而不是由北京當局欽定人選。當然,房地產市場擴張使得居住空間縮小、私有財產神話破滅、年輕世代對未來的不安,也都是運動的複雜成因。
《民現》讓我們看到民眾以什麼樣態現身在雨傘運動中,又或是雨傘運動對世人展現了什麼樣的民主動能?類似雨傘運動的佔領行動普遍對代議政治抱持懷疑態度,不受特定政治勢力操控,沒有強有力的領導中心,甚至組織傾向鬆散,運動過程中不斷衍生矛盾與分化。筆者個人認為這樣的佔領行動普遍具有「安那其」(anarchist)的特質。
包括香港的雨傘運動、台北的太陽花運動、更早的佔領華爾街等,都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即時性與偶發性,充滿異質元素的碰撞,也因此得以產生擴散的力量。《民現》的作者彭麗君還特別強調,佔領行動也是「共居政治」,運動者相互連結形成群體。
也就是說,領特定空間等於是發展出使用和穿越城市的新方式,衝撞挑戰空間的使用權或空間的治理原則,創造出都市空間裡不符合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發展邏輯和效益的不連貫區塊,以及新的生命情境與經驗。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而是需要意志、勇氣與決斷脫離自己的舒適圈,跑到街上「成為民眾」。
如果佔領行動意謂著身體行動、空間使用價值的翻轉或僭越、各種元素即興的拆解、碰撞與組合,那麼,佔領行動必然具有藝術性的本質。《民現》針對雨傘運動的藝術實踐做了相當細緻深入的探討。連儂牆、金鐘佔領區的樓梯各種路障、傘舞、後佔領的紀錄片等等,透過不同的材料與勞動、在不同的時間點以各自的方式「現身」。這些不具有市場經濟價值的藝術實踐現身之處不是美術館、博物館或任何藝術「神聖的殿堂」。
換言之,藝術與抗爭行動的場域不可分離,藝術也不再是任何個別的藝術家和作者所獨佔的產物,而是體現了民眾追求民主的集體意志和慾望,充滿亢奮、焦慮、不確定性,還有希望。如作者彭麗君所說,和雨傘運有關的藝術創作已然是超出實用價值的證言(testimonies),見證了新的群體的生成,也對召喚未來的人們的記憶。
抗爭行動必然是一個觀點、價值觀和力量衝撞的過程,也因此無法免於矛盾、焦慮和不確定感,雨傘運動及其後的抗爭也不例外。《民現》相當關注雨傘運動開始和過程是否有無意識清楚的訴求保持平和,甚至認為運動走向排外性的本土主義,最終以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抑鬱結束,偏離了應有的民主對話多元性和開放性。也對於 2019 年下半年爆發的反逃犯條例抗爭的整個「暴力升溫」的演變過程感到憂慮。
我依稀記得反逃犯條例抗爭中有一句「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這樣的口號。我也一直思索著我們該對國家鎮暴機器和抗爭者有什麼樣不同的要求,和平和暴力的界線如何劃分、誰有話語權和權力劃分。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是否意謂著「例外狀態常態化」取得法律基礎,無辜的小學生都可被逮捕,查無可疑的被自殺案件繼續沒有真相大白的一天,那些被逮捕的年輕人下落依舊不明……我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香港的局勢就有這麼多焦慮和不安,而《民現》的作者彭麗君肯定比我有更深刻複雜的感受。她既是研究者,也是時代的見證者,深刻感受與理解尚在進行中的事件。《民現》是開啟而不是總結!
幾年前台北太陽花運動那一陣子我常被問到太陽花運動改變了什麼,我大概是這樣回答的:
對於一個還在進行中的運動,我無法回答改變了什麼,因為那些改變尚未到來!以任何一種方式參與這次運動的年輕人,他們的生命已被銘刻,他們會因為運動過程中的種種亢奮焦慮恐懼憤怒困惑而對人生有不同的體認他們會繼續訴說與書寫眾多的「小敘述」,不被官方的歷史叫或教科書所收編。我們無須也無權急於為他們決定運動改變了什麼!」
(黃涵榆,《跨界思考》,142)
容許我以這段話向《民現》作者、手民出版社和挺身而出抗爭的香港手足們致敬,你們給予的是希望!
最後我還想說:希望是突破現況政治最重要的原則,是受壓迫者能僅有的力量。
(原載於故事 2020-07-19: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the-appearing-demos-book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