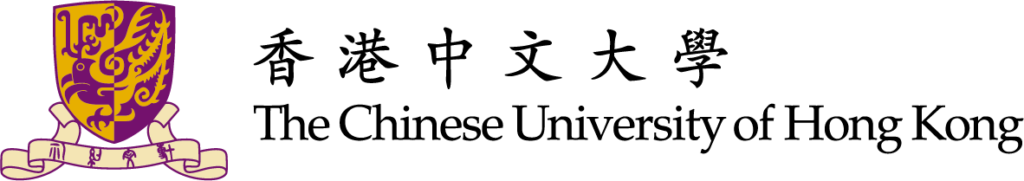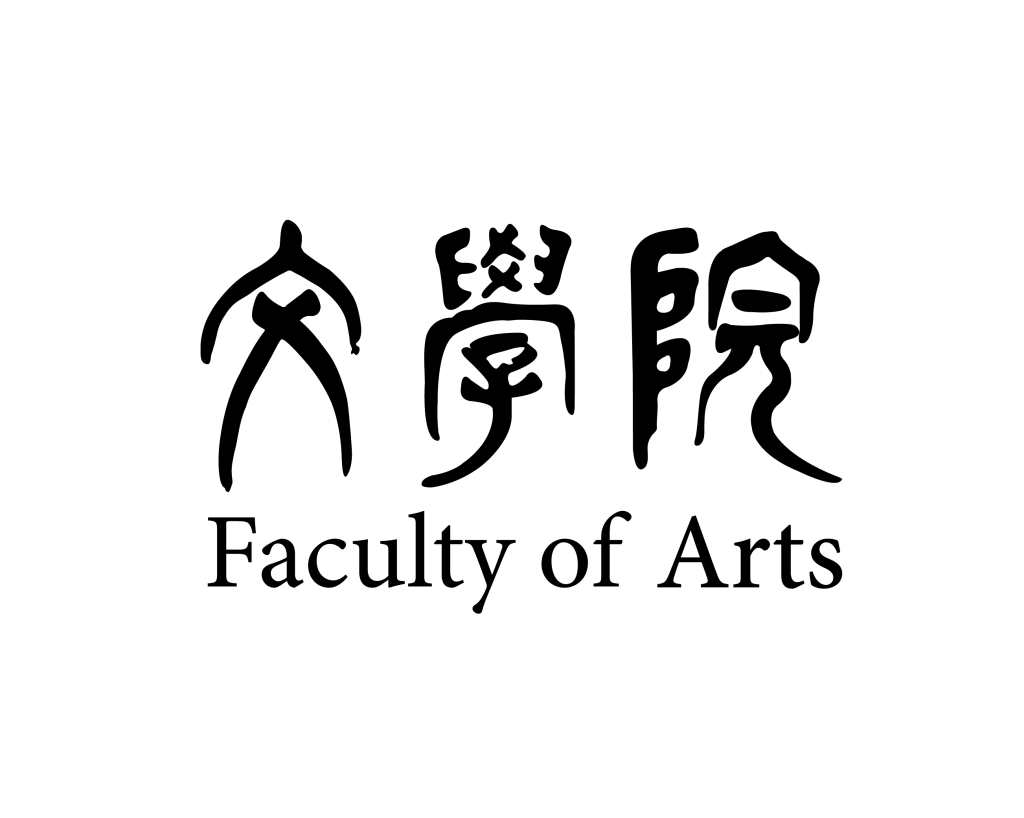Month: April 2022
出櫃,是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嗎?| 林松輝
出櫃,是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嗎? 文// 林松輝 編按:當我們談論出櫃時,是否也考慮過出櫃者所要面對和承擔的一切?2021年,香港文化研究者林松輝推出新書《膠卷同志》,從電影媒介著手、結合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民思想,由前現代中國戲曲中的跨性別演出,一直談至後現代離散中的性向/性相。書中對於出櫃敘事提出了深刻反思,並以許多觀眾熟悉的電影《囍宴》作為文本,來探討那些在出櫃驕傲中被遺忘的聲音與問題。(本文摘錄自《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香港:手民出版社,2021),原題為〈出櫃與同志解放的修辭〉,標題為編者擬,文章經手民出版社授權轉載。) 就同性戀的電影再現而論,對抗負面再現的合理結果,經常是創造出已出櫃的同志角色,畢竟同志解放論述把不出櫃定為自我厭惡的跡象,而出櫃則是發自驕傲的積極行動。過去數十年,出櫃佔據着這樣一個不加質疑——有時候甚至是不可質疑——的地位,不出櫃被視為難以理解的行為。正如莎莉.蒙特(Sally Munt)指出: 基於性相被認為是男、女同志身上最受壓迫的部份,我們因而傾向視之為我們身份的真相,這個誘惑掩蓋了一個恆常不變的假象。對男、女同志而言,「出櫃」等於說出受壓迫的真相……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觀察到,告解與基督教宗教禮儀之間的連繫內存於西方的性相中,告解在結構上與證詞和證人有所關連,亦即一個把經驗化為超驗意義的傳教過程。從這個結合中能清晰看到感受變成了操演:經過物質化和變形,感受得以存在並合法化。(1997,187) 套用笛卡兒的公式,同志解放論述懇求同性戀者宣稱:「我出櫃故我存在。」當同志解放與同志運動如浪潮般湧到華人社會,出櫃也就更普遍地被視為同性戀者的成長儀式(rite of passage)及其個人性傾向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如同在西方所見,當代華人社會中的同性戀者愈發視性傾向為其身份、自我和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中華電影中尋找正面的同性戀再現成為趨勢,出櫃既然被認定具有合法性,並與華人社會對同性戀的壓迫抗衡,若有電影能再現出操演性質強烈的出櫃,便會備受影評人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