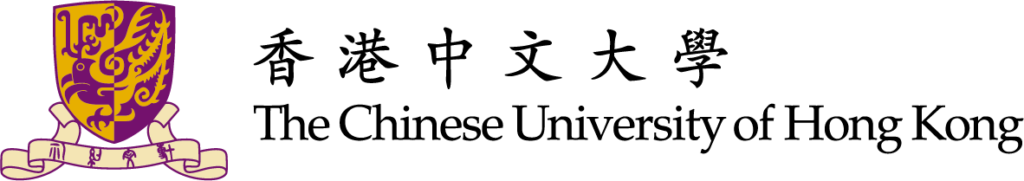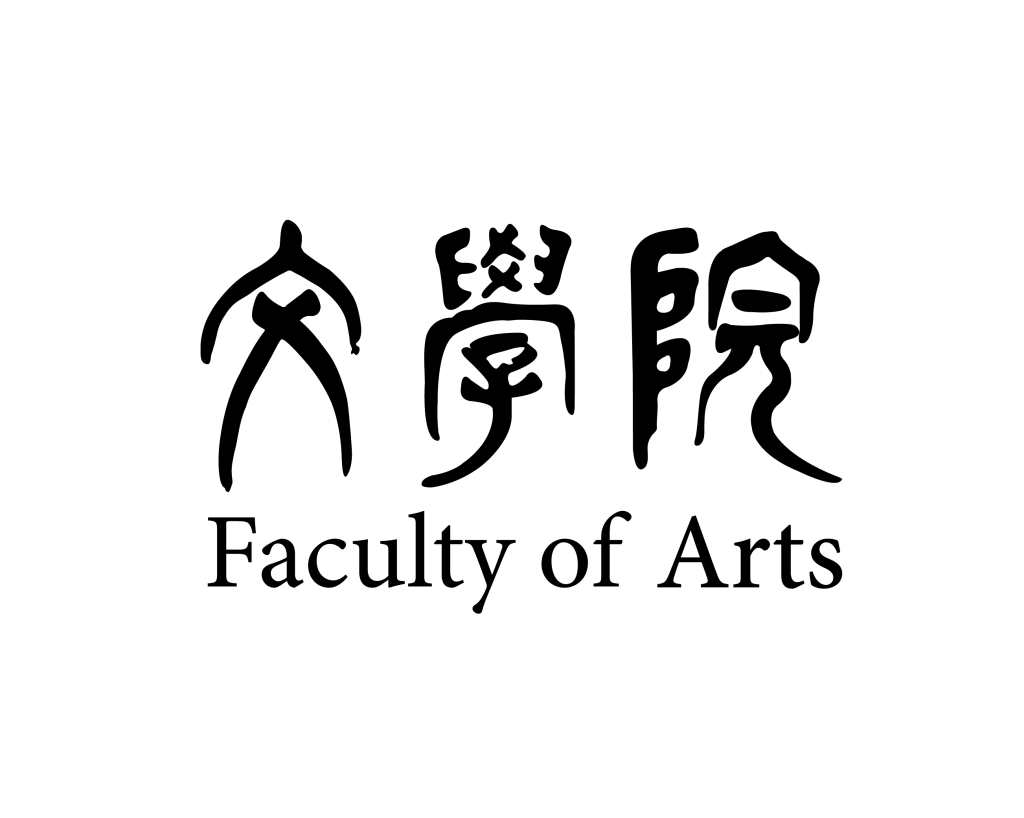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文//李薇婷
編輯//林曉慧
【明報專訊】訪問結束後,彭麗君教授在我手上那本她新近出版的著述扉頁寫上「Enjoy!」一語,真令我想起在求學時期修讀中大文化研究學系時,麗君老師那愉悅樂觀的語氣。而無可否認地,作為學生的我,的確很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在反修例風波未止、疫症全球蔓延的許多個「關鍵十四日」裏,讀到這本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英文版由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出版,中文版將於今個月由手民出版社出版)——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自反修例運動以來,能夠與麗君老師見面的時間竟較平日更多,中大關閉的日子如是,疫症還不太嚴重的日子如是,她總是騎着單車回到中大,在辦公室裏和學生們同在。雨傘過後,零零星星地聽見她總在進行某些研究計劃,同時亦在整理雨傘運動的檔案、在公共平台不斷撰文回應當下,好不忙碌。經歷這半年來的運動,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處世常存困惑,但是,若是有人問我在亂世一名不割席的學者該當如何,我卻難得有確切答案:就像彭麗君老師一樣吧。
疫症時期的中文大學,咖啡店食堂內只得零星員工堂食,與我手上新書封面中人滿的佔領街道照片相映成趣。彭麗君教授的新書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為縱軸,分析雨傘運動所體現的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更試圖與阿倫特討論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思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在民主運動現場發生的矛盾,為香港政體尋找更多的可行道路。雨傘運動相距現今六年,但事過未必境遷,彭麗君新著的成書過程中,正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行文間不乏對2019年的思考。新書中譯本亦將近出爐,由本地獨立出版社、近年專注於理論翻譯、學術出版的手民出版社出版。未翻開著作,光是看看這分析本地社運的著述,在外資書店結業、出版業每况愈下的香港如何出版流通,已有許多意在言外。研究生如我,阿倫特是傘後鬱悶時期、同儕間競相閱讀的大熱理論家,惟用之分析雨傘,甚至與之商榷,交出厚重研究,彭麗君則是第一人。
傘後困頓 與阿倫特對話
大抵也是傘後困頓的緣故,彭麗君才希望與阿倫特對話:「面對2014、2015年間的各種運動,我內心困惑,腦海裏有許多問題,試圖透過寫作來解決。由這個簡單的動機,選擇了與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展開對話。我在寫作期間一度掙扎於直接研究阿倫特抑或一本關於香港的書。但我終究希望以香港作主角,因為這始終是我的初衷。」站在2019年回望雨傘,輿論多認為雨傘運動是失敗的,然而,彭麗君卻覺得一場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並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成敗來論斷。對她而言,與阿倫特的對話之所以有意思,亦在於好好總結一次傘運對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的意義,以開啟更廣闊的前路:「我不認為這場運動失敗。對於許多和理非而言,雨傘運動某程度上啟發了他們可以如何走民主運動的路。許多人認為雨傘運動『做唔到嘢』,但換了方式後是否又算是『做到嘢』?我想許多人都被困在香港的困局裏,走不出去。面對困局,更不應簡單地劃分輸贏。現在,我們雖然不能說反修例運動已經完結了,但是,香港仍然重複着雨傘時期的困局。」把抗命的心志植根於腦海,是傘運教會我們的一課,我想這一點沒有太多人會反對。但除了意志上的果實,香港人究竟從傘運得到什麼?彭麗君的書裏說,透過現身於街道的人民群體,我們不但再次確認「香港」這個社群的存在,還得到了一場「共居」事件(communal event)的短暫實驗。在我看來,彭麗君新著的價值很大程度就在於此。2019年看過太多眼前路,我們彷彿忘記了如影隨形的沉重的身後身。
政治行動 無法不帶情緒
動輒得咎,或許是許多公共評論空間參與者在這段時期的共通體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出謀獻策,隨之而來的便是策略檢討以及「不完美,可接受」,輿論空間一直子彈橫飛。儘管一月以來疫症肆虐,各種抗爭行動略為平靜下來,但是,不同議題爭論繼續在公共平台沸沸揚揚。在這段期間,彭麗君倒是發表了兩篇言簡意賅的文章,既批評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建構,也在肯定港人的抗爭創意同時,再思反修例運動中左翼的位置。她為文章留下一句反高潮的結尾,坦率地說攬炒之後「也不就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當時我為老師這種平淡而堅定的游刃有餘感到驚訝而拜服,讀過新書,明白到阿倫特的政治理論大抵有功有勞。
「研究當代議題,事情仍舊在發展當中,拿揑距離很困難。我想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困境。但這次研究和書寫最大的挑戰,倒不是跟不斷發展的事件對話,而是面對當中排山倒海的複雜情緒。不過,這些情緒同時給予我很大的體會。大家困在沒出路的焦慮中,若這些情緒是共同困局,我該如何向這種情緒提出問題?」彭麗君雖然未有參與論爭,卻一直留意各種議論的發展。在她看來,困局焦慮衍生的情緒暗中影響着輿論發酵。她要做的不是忽略這些在群眾運動中必然存在的元素,而是在阿倫特的理論中尋找解決之道。「阿倫特的思想中有些線索很值得後學追蹤。其中一條是『私人—社會—政治』。由最初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到最後談論康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她都掙扎如何把三者分開處理,尤其不要讓個人情緒和私利進入政治空間。」彭麗君解釋,阿倫特了解到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走進群體的現身空間,從而影響公共空間應有的平等性和多元性,情緒就是其中重點。於是,她窮盡畢生思考如何讓民眾現身的場域變得純粹,避免影響運動群眾的行動走向被私人恩怨、以至那些操控擺佈這些情緒的政權所綁架。但是,麗君並不完全同意這一點:「這是我和她最大的分歧。我想大家都明白攜帶過多情緒進入現身空間會將之變成泥漿,但現實就是,人根本無法不帶任何情緒和私心進行政治行動。在這本書內,這一點和阿倫特的商榷很重要的。如何在得知有問題存在的情况下繼續前行,是我很想研究的問題。」
批運動民粹化 言之過早
情緒似乎成了運動無法避開的關鍵詞,有輿論甚至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走向民粹化。但是,麗君認為要批評反修例是一場民粹運動言之過早:「民粹主義通常有三個準則,第一,對於精英的怨恨,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沒有的,從雨傘到反修例都有不同階層的參與,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第二,有確切的領袖,這亦是反修例運動中看不到的,我們甚至會強調自己『無大台』。第三,民粹主義通常發生在某種代議政體下,因為大部分的民粹領袖都是通過選舉產生。這三項條件都令我們不宜把香港眼下的運動簡單地評作民粹。民粹主義的發展有其歷史軌迹,對很多西方評論者來講,民粹是民主的歧途,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民粹也可能團結人民對抗權貴,這是左翼民粹。但香港都不是這種狀况。」對彭麗君而言,許多在香港運動中的問題,其實都是全球城市同樣面對的問題。
只是,彭麗君強調,人們也必須認清「暴力」的概念:「阿倫特也研究暴力在六十年代美國和西方的左翼運動的產生。她認為人們在運動中使用暴力希望達至某種目的,那是人們不了解暴力。她認為暴力不能作為政治方法,因為暴力是無法控制的。當我們將之用作『手段』,這『手段』最後往往取代初衷,成為目的。但阿倫特也沒有完全否認運用暴力的政治意義,就是當我們面對巨大的權力和邪惡時,要與之最後一搏可能也是必要,不過我們要了解當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在阿倫特的論述中,暴力是具破壞性的,不但破壞所謂敵方,同時撼動初衷,她補充:「某程度上,阿倫特說得對,到了某個境地,我們便要回到可以溝通的位置,放下情緒。但是,假如我們純粹地譴責那些帶着情緒進入現身空間的民眾,只會令世界更加無法溝通。你要尊重別人的情緒,亦要告訴他們過多的情緒投放是行不通的,這是我感覺到眼下香港最大的困局所在。即是,我們如何在『不割席』的情况下,告訴人們,我們需要坐下來好好溝通。」帶着閱讀阿倫特的體會,彭麗君在新書內分析雨傘佔領區在「溝通」上的各種嘗試。在一個民現空間(appearing demos),人們沒有因為情緒而放棄溝通,這大抵是反修例運動中各種階層、角色都需要鄭重地重新納入考量的一點「遺產」。
以「城邦」為藍圖的「城市權」
但是,究竟在同一城市內的各種群體應該如何溝通,怎樣共居?部分港人開始認為香港正受中國二次殖民,在這種「極端」狀態下談「共居」,是否空想?對於香港現階段的情况,彭麗君直言不宜簡單地以「二次殖民」概括,因為相比起「殖民主義」這個相對古舊的概念,香港作為全球化底下的資本主義城市,情况實在是更為複雜。「在某些全球左翼眼中,香港仍在殖民狀態,但殖民主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香港只是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隻棋子。而香港這邊廂又有部分人認為正經歷中國的二次殖民。我覺得殖民也好,後殖民也好,都不能最有效分析現在香港與西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但我更願意用『城邦』來理解香港。」彭麗君解釋,「城邦」的概念對香港有啟發性,是因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個沒有主權但有自治實體的城市。
不過,有別於陳雲回到華夏正統的城邦論,對應香港的歷史脈絡,彭麗君在新書中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香港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城市作範例,解決令全球都共同感到頭痛的、由現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所謂necessary evil所帶來的各種惡果。彭麗君肯定「國家」、「民族」甚至「民族主義」都曾經是很有活力的概念,帶動許多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反殖戰爭:「我相信沒有任何一種概念可以說只是絕對的壞,或是完全地好。但是在香港,我要面對的是兩個問題,一,假如中國正以一種官方民族主義來影響香港,我們是否應該用同一個方法來應付?二,香港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從歷史脈絡中深挖後再思考前路?」她強調,「國家」、「民族」其實是有許多層次的概念。與其重新建構新的民族論,不如正視香港作為「城市」的身分:「中國曾經希望以上海、深圳來重新『打造』一個香港,但這麼多年來都未見成功。怎可能複製一個城市呢?同樣地,我們為何要強行重新建立一樣香港歷史上沒有的東西?相反,我們擁有的是多年來作為城市的城邦形態。既然認為香港是屬於『我們的』,不妨從香港自身的歷史挖掘一些概念,正視『城市』這個概念。」城市權的提出,是企圖建立一個存在於現代國家體制下的擁有民主的城市,把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可行單位。
與「不喜歡」的群體「共居」
談及政治共同體,不難令人聯想起梁繼平等學苑編輯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內文不斷提出以民族及現代國家體制作為基礎,為香港建立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又有別於此,彭麗君在書中把「主權」理解為眾多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ies)並存的狀態,不同於民族所要求的統一,着重不同群體之間的協商。「英殖時期,『主權』由英女王的頭像所代表,人們繼續自己的生活,似乎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的香港,理應較英殖時期更加自由民主,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我們可否思考『主權』的不同層次呢?阿倫特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共居』。我們要回去思考人們在同一個城市出入,是否可以共同生活。這甚至不需要一個『共同體』才可實行。」的確,許多人認為香港是移民城市,或是難民城市,事實上,全球化語境下,每一個城市都有着移居者,問題的關鍵除了認清這事實之外,還在於如何與移居群體「共居」。「書的第六章中,我談及right to stay and right to move,人們可以因應各自的需要,選擇進出這個城市。新一代香港人對這個社會發展出很大的認同,這是很可貴的,大家希望共同努力保住這個『家』,這也是一種很強力的互相賦權,但如果這變成一種惡性綑綁和排外,忘記香港本身一種共居的狀態,我們只會走向更差的境地。香港的居民很長時間都在移民、返鄉和移動的狀態中。也有很多人來香港,從跨國資本家到第三世界難民都有,人來人往或許未必令一個城市變好,但也未必會變差。然後,我們再想像國家是什麼,甚至離開國家體制來思考這種共居的概念。」彭麗君補充,她一再重申希望大家離開國家體制作為前設,更多地想像政治共同體的其他可能性。
在一個能夠和現存的國家協商主權的城市裏共居,其實很理想。但是,讀畢全書再回望現實,這落差變得更為明顯。就算不以殖民狀况來思考香港現狀,人們仍然難以應對一些新政策的變動甚至政策傾斜。事實上,反修例運動就是一場由法律變動而衍生的全民運動。無法包容,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彭麗君說,不如我們學習和一群我們不喜歡的人談論共居吧:「無論左翼、右翼,某程度上都很理想化。你或許會覺得『共居』有點『戇居』,但是,不共居的話,我們可以走到哪裏去?現實就是,全世界都有海量的問題,這是人的生存狀况啊。阿倫特提出共居的概念,例子是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這兩個找不到一點歷史文化共通、甚至互相仇恨的種群都必須找方法暫時共居,為何香港不行?」
和一個威權政體協商主權,不是與虎謀皮嗎?訪問期間,我多次向麗君老師投以困惑的眼神。而麗君老師亦很快捕捉到我的疑問:「的確係好理想化,仲好大機會無法實現,哈哈!你再問我,答案可能好老套:盡做。」是的,為香港甚至世界各個城市想像更多可行出口,何妨?彭麗君不但在新著中大膽提出以城邦為藍圖、自治為目標的「城市權」,同時反思「法治」與香港社會運動的關係,不無反思與啟發。「坦白講,如果可以的話,我只想好好地讀書,當個純粹的讀書人。」麗君老師輕鬆地笑了一笑,說自己不想當什麼知識分子,只想當個讀書人。我聽着這看似簡單的願望,在眼下這壓抑的時刻,竟覺奢侈非常。
■答: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系教授。研究範疇為現當代中國和香港文化及政治。
■問:李薇婷,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文學文化評論人。
(原載於明報副刊 星期日生活2020-04-05: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00405/s00005/1586023434545/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fbclid=IwAR1_eWmnwGG3Nq5mP63CSezv_dSyKklunlIeVtjltz2gablQYcWsus1PG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