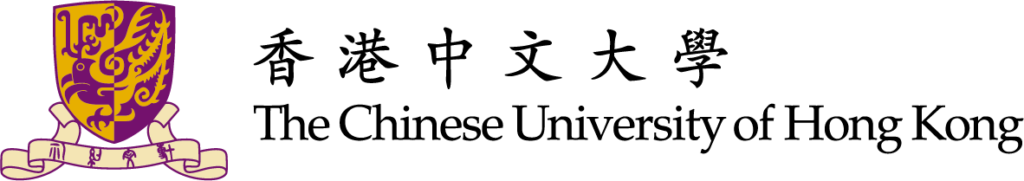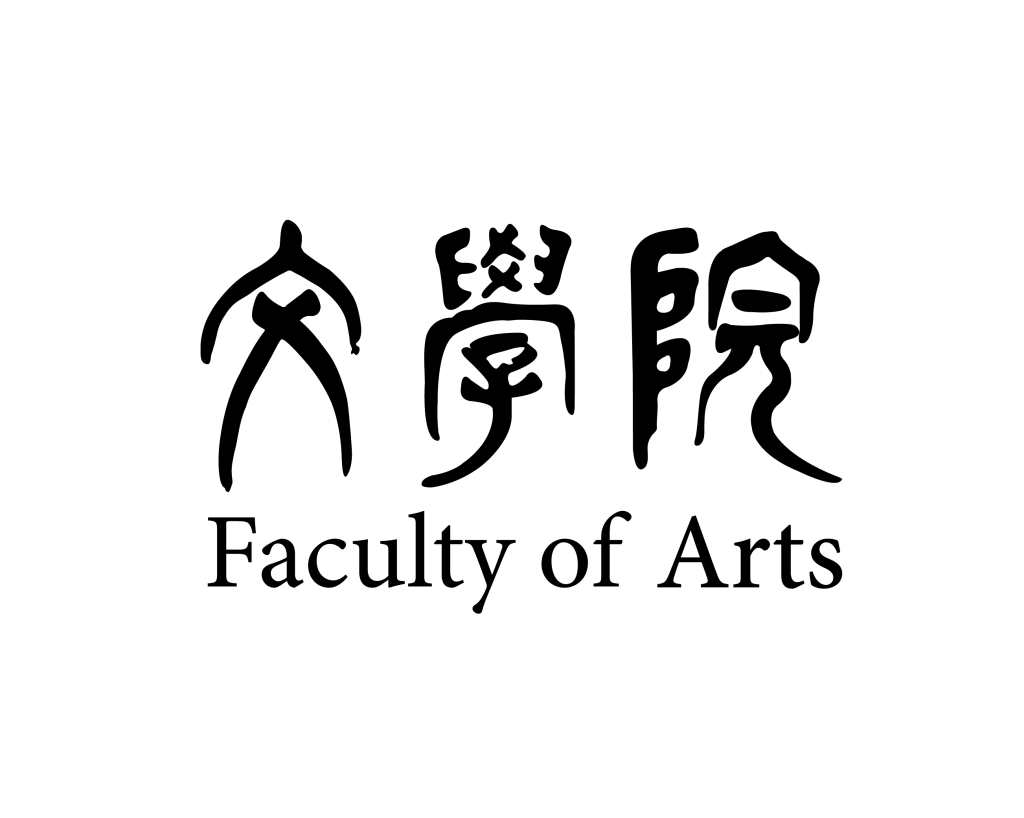所謂「參與式審查」,是指網絡上的個人或群體,在國家政策和數字平台設計的推動下,積極地參與分散性審查的行爲。
特約撰稿人 白露 譚佳
時間稍稍回撥五年。2018年11月16日,一條新聞從耽美圈席捲至公眾視野:以創作網絡耽美色情小説而聞名的中國耽美作者天一,因其小說《攻佔》涉及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並處罰金。
這一嚴厲的判決震驚了中國的耽美粉絲和普通民衆,並被國際新聞媒體廣泛報道。雖然出版淫穢物品在中國是違法行爲,但在網絡上創作和發佈情色内容乃至影印「個人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處於灰色地帶,很少導致嚴重的法律後果。
天一的被捕是被舉報的後果,在中國大陸掀開了延續至今的圍繞「舉報」的實踐和討論。除了廣受關注的天一案,其他中國耽美作者也因他人舉報而受到罰款、逮捕,乃至判刑。相較於天一遭到耽美圈外人的舉報,許多其他耽美作者陷入了因圈内糾紛而被舉報的境地,這些舉報很有可能來自耽美讀者或創作者,所謂「圈内人」。
其中後果最為嚴重的一起圈內舉報,便是2019年被判刑四年的「深海先生案」。據網絡流傳的說法,耽美作者燁風遲因被耽美作者深海先生暗示抄襲後者作品,而對後者及其家人進行報復性的實名舉報,舉報深海先生作品為淫穢出版物,深海先生在被關押近兩年後以非法經營罪獲刑四年。比起「天一案」作為外部舉報帶給耽美愛好者「小心圈外人」的警示,「深海先生案」則成為了用舉報解決內部爭執的風氣之先。
天一案和深海先生案,體現出中國大陸互聯網審查制度和粉絲群體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轉變。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大陸數以千萬記的粉絲為衆多歌手、演員和其他領域的名人的商業成功做出了卓越貢獻,粉絲文化也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粉絲一樣,中國大陸粉絲的參與有多種形式,包括參與相關話題的討論、進行二次創作表達喜愛並提高影響力、在綫上綫下活動中表示支持、購買相關的贊助商品和廣告位,等等。
但對耽美作者的定罪則體現了中國粉絲面對的特殊處境:政府對網絡内容不斷加强的審查和平台在監管下進一步收緊的内部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耽美社群中大量成員反對此種惡意舉報行為並為受害者積極聲援,但這種超高效力的「戰勝對手」的方式已經進入眾人的視野,「參與式審查」的程序與效力已經在了解事件的過程中被更多人習得。由於舉報成為打壓「敵方」的有力武器,於是戰況愈演愈烈,逐漸成爲粉絲日常需要面對乃至使用的一部分「工具」。論壇和社交媒體平台也不斷改變頁面構成,把舉報功能放在方便快捷的位置以供使用。
- 從參與式文化到參與式審查:中國網絡酷兒粉絲群體
學者們在談到粉絲的參與式文化,以及酷兒性時往往關注其積極的一面,而不太進步的方面卻時常被忽視。
在原本的意義上,「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一詞被用來描述粉絲在新舊媒體融合文化背景下的活動和創作,這個文化生產和傳播的模式在於强調觀衆的主動性和多元參與,已有相當多的學者從各個角度展開論述。作爲酷兒粉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耽美文化通過建構與日常不相匹配的男性氣概,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規範性的文化預設和既有的社會等級秩序,創造出一種批判性的酷兒詮釋(Gong, 2017; Santos, 2020)。耽美文化的酷兒性不僅體現在文本中的男性間的浪漫愛與情色内容,也在於受衆的多元的參與方式、社群組織方式、身份及情欲探索路徑的開放性與不被定義。
學者們在談到粉絲的參與式文化,以及酷兒性時往往關注其積極的一面,而不太進步的方面卻時常被忽視。在既有的耽美研究中,耽美粉絲經常被視爲正統文化和社會規範的挑戰者、國家文化生產系統的受害者,或是在夾縫中逃避審查的積極實踐者,而較少被視爲審查的參與者。
但由於中國大陸的商業平台,往往通過功能設計和内容審查來執行和維繫國家審查制度,平台用戶便也被鼓勵成爲審查的合作者,以達到平台更安全運營的目的。而面對日益嚴格的國家審查政策,粉絲現在可能會繞過平台,直接向政府監管機構進行舉報,引發政府對平台進行處罰,從而推動平台在内容審查方面更加嚴格。
然而粉絲之間的相互審查則以更加普通和日常的形式發生在各種數字平台上。由此,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學者譚佳與其合作者通過建立和使用「參與式審查」(participatory censorship)這一術語,來概念化用戶和審查制度之間的動態關聯(Wang & Tan, 2023)。所謂「參與式審查」,是指網絡上的個人或群體,在國家政策和數字平台設計的推動下,積極地參與分散性審查的行爲。不同於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審查,參與式審查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機制,實現於普通個體的日常活動,換言之,也依賴於特定數字平台的功能設計。
- 「遇到黑子就舉報」:去中心化的審查和内容仲裁
即便當時不存在與其他粉絲的爭執,社群內部的粉絲也時刻保持著不限內容範疇的互相審視狀態,使彼此的言行處於控制之中。參與式審查在日常實踐裡落到實處。
2018年6月13日,耽美改編劇《鎮魂》在優酷視頻上綫。這部劇是由晉江超人氣作者priest於2013年完成的同名耽美小說改編而成,原小說在晉江文學城的點擊率高達1100萬以上,在耽美愛好者中流傳甚廣。隨著劇集的播出,劇情、角色和演員在微博熱搜頻繁上榜,主角CP「巍瀾」的話題在6月21日便超過「錘基」佔據微博CP榜首位。截止7月25日收官,該劇的播放量高達27億,微博話題達12.5億。耽美改編劇《鎮魂》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照亮了之後的耽美小說版權販賣和影視化之路,後續雖有政策上的收緊和暫時的中斷,已經播出的另外幾部耽改劇所收穫的商業上的成功是不可否認的(註:「錘基」,即「雷神」與「洛基」的耽美配對,兩位角色出自漫威電影與漫畫)。
「巍瀾」相關的超話中,最為活躍的是「巍瀾」超話、「巍瀾衍生」超話和「劇版巍瀾」超話,每個超話都在置頂帖或管理帖中明確了各自的發帖限制與規則,並有主持人負責維護超話的規定得以執行。超話的規則中均包括:1、禁止拆逆,2、禁止盜圖,3、禁止盜文,4、禁止發廣告,5、禁止引戰罵人,6、禁止踩一捧一,7、禁止暴力言行。三個超話的區別在於「巍瀾」超話禁止出現真人相關內容(但在運作中並沒能夠執行,因而仍是聚集粉絲最多的「超話」),「巍瀾衍生」超話覆蓋從角色到演員包括其他作品在內的一切相關內容,「劇版巍瀾」超話僅限於《鎮魂》一劇中角色相關內容。
由此可見,超話對粉絲的約束主要是內向型的——降低矛盾糾紛的可能、減少與其他相關內容的互動,鼓勵圍繞話題本身的自我增殖。對待相異的內容,舉報是最常見且高效的應對方式。在超話的精華內容中,主持人有專門發帖,明確聲明「遇到黑就舉報」、「截圖私信管理」等字樣,評論裡的粉絲則紛紛留下不合規範的言論的網址,留待主持人處理。
筆者在追蹤觀察中,發現評論中的內容能在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內得到解決——內容被刪除,發帖人被屏蔽在超話之外,無法在此社區內評論或發言。早期的內容以拆逆CP居多,這一部分被逐漸驅逐出社區之後,內容就多數是營銷號在社區內打廣告,以及少量的無授權搬運信息(註:「拆(CP)」是指解除二人的情侶配對,與他人配對;「逆(CP)」則指轉變二人的攻受屬性。後文出現的「嗑(CP)」亦是粉絲術語,指投入地喜歡,如同「嗑藥」一般沉醉)。
與求助微博管理以得到反饋相比,社區內部的管理效率高得驚人。「遇到黑就舉報」一句話概括了整個過程:粉絲會通過搜索關鍵字的方式瀏覽CP某方的信息,看到負面評價時,程度較輕就通過留言評論「控評」來扭轉印象,程度較重則直接舉報,並把網址放到社區內部,圈內成員見到便會跟著舉報,有時亦有專門的「反黑組」每日打卡行動,通過增加舉報次數來提高舉報的成功率。
針對性不強的舉報可能並不會帶來處罰結果,在廣場上通過誇張而正式的遣詞造句大肆宣揚對某一群體的舉報,更多的是向對方造成心理震懾的效果。而若能提供違反微博規則的詳細信息截圖,數量較多的舉報會導致被舉報者賬號異常,有被禁言甚至封號的可能。
但這類信息通常不包括色情信息,而是指時政相關的內容,因而意圖舉報個人時,舉報者可能並不單單挑選關於CP的內容,而是整個地檢視這個賬號所發言論。這種情況會導致被舉報者所處的社群無法展開支援,更可能的情況是撇清與被舉報者的關係,從而避免牽涉自身社群。這就導致即便當時不存在與其他粉絲的爭執,社群內部的粉絲也時刻保持著不限內容範疇的互相審視狀態,使彼此的言行處於控制之中。參與式審查在日常實踐裡落到實處。
- 壓抑酷兒性:在耽美商業化中展開審查的粉絲們
耽美改編劇與耽美小説原作相比,往往將同性戀愛的部分隱而不談,或以友情取而代之,同時保留曖昧的場景和經典段落,以便粉絲能夠想象缺失的情節並用酷兒視角重新詮釋故事。
耽美改編劇與耽美小説原作相比,往往將同性戀愛的部分隱而不談,或以友情取而代之,同時保留曖昧的場景和經典段落,以便粉絲能夠想象缺失的情節並用酷兒視角重新詮釋故事。因爲涉及到政府和網絡平台的審查,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内容創作者們需要主動展開自我審查,檢視其中的風險。
儘管在改編中已經淡化了同性戀愛主題,《鎮魂》仍然在2018年8月2日被播放平台優酷突然下架,8月9日新浪微博關於《鎮魂》的話題也被封禁(後於8月18日解封)。這一系列操作再次引起粉絲的討論。直到11月10日,該劇經過重新剪輯,刪除了一些重要的親密場景後才再次上線。
嚴格的政府和平台審查環境,使粉絲的參與式審查行為更加普遍和突出。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在「巍瀾超话」上的討論都在試圖規範和約束粉絲的發言。當時的粉絲們感到困惑無助,不斷詢問平台和有關部門為何下架《鎮魂》,抱怨審查政策和有害的商業競爭環境。一位較有影響力的粉絲發微博倡議粉絲不要點擊熱搜「#镇魂下架#」,因為「是優酷在做畫質優化」,也不要向優酷和廣電文化局抱怨此事,避免「本來沒被禁的,真的被禁了」。這些粉絲們情願相信,《鎮魂》的下架是一種保護性下架,以防止有關部門的注意,從而導致真正的封禁。
出於對耽改劇和參演演員的保護,很多粉絲停止或刪除了自己的抱怨,並將這種考量講述給更多的圈内人,正如許多其他關於被舉報的案例中的粉絲一樣。在這個過程中,參與式審查制定了小範圍内的規則,限定了討論的範圍,試圖限制性取向和性關係相關的酷兒表達,以支持一個在商業上更有價值的粉絲社群。
學者Ng和Li(2020)在研究《鎮魂》粉絲群體的研究中指出了其中的自我審查現象,即粉絲們大多避免直接談及兩位演員之間的同性浪漫愛,而是使用「社會主義兄弟情」來形容兩個角色,「巧妙地將異性戀規範化的社會主義中國和同性戀的酷兒思想結合起來,同時為粉絲提供至少暫時的免受審查的保護。」除此之外,參與式審查的研究者還觀察到了更爲複雜的情況:粉絲會使用在上一節提到的包括舉報在内的功能來限制和規範酷兒表達。
特定的話語如同禁區,斷章取義地搜檢出來就可以作為非粉絲乃至黑子的明證,從而進行驅逐甚至舉報。而且這種鑒定是無視時間性的,不論何時留下的痕跡、只要留在可檢視的數據庫上,都有被揭發的可能。
首先,不同類型的粉絲之間存在等級秩序。一如其他劇集,《鎮魂》的粉絲類型多元,包括演員個人的粉絲、巍瀾CP粉絲和其他粉絲。一位受訪者表示,「當我們嗑(喜歡)巍瀾時,我們只能悄悄地嗑演員真人CP。但是,我們不敢在CP視頻或者超話中直接提。我們只能用巍瀾這個名字的超話,因為每次建立演員CP超話,它都會被唯粉給舉報沒。」
這位受訪者的經歷顯示,由於其他人的舉報,耽美CP超話的炸號在微博很常見。雖然「圈地自萌」和謹言慎行是耽美粉絲規避不可預測的國家審查的一種策略,但這也會加劇異性戀霸權和對性別的管制,同時強化了官方對監控、安全和何爲「正常」的話語的規訓。在2019年,多個耽美CP超話被以「損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破壞網絡環境的和諧」的名義舉報,而這正是「淨網行動中」的官方話語,大量類似投訴導致了許多CP超話的解散。這清楚地說明了粉絲之間的舉報如何限制了酷兒表達的話語範圍,粉絲又如何成為擴大官方審查權力的審查參與者。
即使在倖存下來的CP超話中,粉絲關注的對象往往是虛構角色,而非真人演員。正如另一位受訪者指出的:「無論是巍瀾超話還是巍瀾衍生超話,都不允許RPS(真人耽美同人)內容,所以粉絲們都按照規定做,不會在其中發布相關內容」。其中一個原因是,當CP粉絲開始搞RPS時,演員的粉絲可能會因恐同等原因而感到被冒犯或出於「保護演員職業生涯」的目的,舉報這些帖子或超話。例如,在2020年發生的肖戰粉絲舉報AO3網站事件便是實例之一。
除此之外,在CP粉絲圈内部的嚴格管制,也可能會將因愛而匯聚的耽美空間變成一個懲罰的空間。一位深度參與巍瀾粉絲活動的受訪者講述了她退圈的起因:她和喜歡的作者進行溝通時用詞不當,使用了通常被非CP粉或黑粉使用的詞語,儘管是她無心之失,但她在評論裡被其他人攻擊「裝什麼粉」、「不愛看別來看啊」,並在進行解釋時發現已被作者拉黑。在經歷過喜歡的創作者因被舉報和粉絲爭鬥而退圈之後的她,不願再自證身份,於是也黯然退圈。
這次「被自己人背叛」的經歷,除卻體現激烈的CP粉與拆家或唯粉的對抗之外,更能說明CP粉內部的話語限制和規範——默認粉絲需要熟知CP及粉絲圈相關的知識,將特定詞彙視為「粉」與「黑」的界限,以言論而非情感作為區隔,嚴格地遵守著粉絲排除規範。特定的話語如同禁區,斷章取義地搜檢出來就可以作為非粉絲乃至黑子的明證,從而進行驅逐甚至舉報。而且這種鑒定是無視時間性的,不論何時留下的痕跡、只要留在可檢視的數據庫上,都有被揭發的可能。
粉絲被認為隨時接受對過往「不當」言論的質問是合理的。由於平台設計通常缺乏有效的上訴系統,平台變成了一個懲罰性的空間,經常讓用戶感到困惑和沮喪(West, 2018)。
- 游牧的酷兒:反對商業化和審查制度的耽美粉絲實踐
正如另一位受訪者所説:「越屏蔽我越要寫,越多男的要(在我的小説中)做愛。」
隨著參與式審查在耽美粉絲群體中廣泛出現,替代性的策略被粉絲們摸索著創造了出來。例如,粉絲們采用各種替換敏感詞的方法,或以翻轉的圖片、加密的網盤、聊天群等形式傳播,從而保證酷兒内容能夠被完整地發表和傳閲。
由於參與式審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平台設計,例如舉報功能和敏感詞限制,也有許多粉絲轉向海外平台或其他非營利性網站,以表達他們對現有平台審查的不滿。2020年到2023年間,耽美粉絲們幾次發起對以同人文發家的網易博客平台Lofter的抵制和棄用,越來越多的耽美粉絲轉向使用AO3(包括其鏡像網站)、搭建Wordpress個人網站,以及其他新平台進行寫作和交流。
儘管這些新平台的寬鬆環境得益於其自身的小衆和不受關注,亦發生過數次背離承諾加强審查的事件,或運營一定階段後被迫終止,但在這個遷移的過程中耽美粉絲們(或者説更大範疇上的同人女們)也愈發清醒地認識到自身處境。這些游擊隊一般的游牧實踐也促使粉絲們在近乎壟斷的平台之外,探索各自的離散道路,以實現創作和閲讀自由。
除了使用替代性平台,其他的游牧戰術也被發明出來抵制網絡審查。面對創作和消費色情内容的污名,一些耽美粉絲發起了書寫「站街文」的號召,發出「每一對CP都有屬於自己的站街文」的呼籲,鼓勵耽美粉絲大膽擁抱禁忌、拒絕性羞恥。這場寫作運動暫時開啓了不受審查的網絡空間,作爲商業化的審查空間的替代。雖然運動較爲短暫,但因其組織方式的高度靈活和隱蔽,使它相對較難被舉報。儘管其中一些情色作品最終會被平台刪除,創作者的賬號也會被封禁,但這些粉絲仍會重新創建新的賬號繼續寫作。正如另一位受訪者所説:「越屏蔽我越要寫,越多男的要(在我的小説中)做愛。」
除了粉絲群體不斷在不同數字平台間遷移流浪,以及這個過程中創作和搬運的作品,很多同人女還發起了「用魔法打敗魔法」式的對新浪微博、淘寶店家等多個主體的商業運營表達抗議。以2020年肖戰粉絲舉報AO3網站事件的後續發展為例,由耽美粉絲發起並逐漸在網絡擴散開來的抵制肖戰商業代言、購買替代性競品、向代言商家索要過往消費的實體發票從而增加商家人工成本等行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效果,影響了一些商家及品牌商。在227事件後,在大量消費者的投訴下,OLAY、佳潔士、蒙牛等計劃或已經與肖戰合作的公司紛紛更換代言人或撤回了廣告。
儘管這種行動對耽美商業化的整體趨勢並不能造成轉折性的影響,這些嘗試中也可能存在種種問題,以至於結果與發起的初衷相悖,但這些游牧性的實踐畢竟動搖了耽美群體被期待規訓出的同質性和維穩性,並且在耽美商業化的背景下不斷摸索著創造性的替代實踐。
結語:中國和耽美之外的參與式審查
參與式審查的提出,一方面是為耽美粉絲的行動提供一種與社會和時代背景相關聯的說明解釋,另一方面,這種並非耽美群體獨有的現象也能為理解更多網絡事件乃至人們生活和行動中的具體變化提供認知上的借鑒。
對於耽美社群而言,由於耽美改編劇是由資本引導的商業化產品,耽美在進入大眾視野的同時不得不被閹割掉核心,創作尺度不斷縮窄,壓抑了具有挑戰性和抵抗性題材的作品的產生與傳播。
另一方面,新成員的大量湧入模糊了原本的社區共識,審查制度與舉報手段也損害了耽美作為亞文化群體內在原有的自治與自淨能力,社區的生態平衡被打破,瀕臨失控。參與式審查在平台功能的推動下,隨著耽美文化邊界擴張而不斷擴散,被更多的耽美愛好者習得,乃至將其視為文化經驗中的一部分,而不去質疑其產生的由來與合理性。與此同時,公權力的延伸介入也進一步破壞了耽美社群的生態,與日俱增的舉報是對集體意義建構的否認,也容易導向內容同質化和對抵抗話語的刻意迴避,會影響到耽美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雖然學者對參與式審查的概念界定和理解,是從中國耽美粉絲群體相關的討論中得出的,但這一概念也可以被考慮應用於更廣泛的粉絲文化乃至網絡文化現象中。參與式審查指向的是一個越來越複雜的景觀,國家治理、商業運營與粉絲參與交相錯雜。參與式審查因其對被舉報者高效的負面影響而具有強大的傳播力,並不僅僅在耽美群體中愈發普遍,而是在整個當代網絡社交媒體上日益顯形。
從中國大陸各個社交平台的「舉報炸號」、因不同類型程度定義下的「辱華」行為而在民眾間發起的對商業品牌與文藝作品的抵制,到2020年全球熱議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參與式審查的影子暗藏在這些事件的背後,由此可見其被進一步發展推論的廣泛潛力。但同時,本文選擇耽美群體展開分析,並非意在宣告這一現象是由耽美群體中誕生並擴散出去的。參與式審查的提出,一方面是為耽美粉絲的行動提供一種與社會和時代背景相關聯的說明解釋,另一方面,這種並非耽美群體獨有的現象也能為理解更多網絡事件乃至人們生活和行動中的具體變化提供認知上的借鑒。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一方面於2021年開展了「清朗 ‧『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在粉絲經濟中介入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以保護未成年人爲名整頓產業鏈的同時瓦解自我組織的粉絲群體;另一方面又積極採取「粉圈治理」(fandom governance)的模式,使用可愛形象來培養粉絲受衆的民族主義認同(Wong et al., 2021)。
越來越多的國家也正在借鑒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模式。除了亞洲和南美洲的關鍵詞過濾算法案之外,俄羅斯和尼日利亞也在使用類似中國互聯網防火墻的系統。在這個更大的背景下,參與式審查的形式和程度,或者粉絲參與如何與國家治理和商業運營纏結,在其他國家和文化背景中仍有待探索。
(本文內容主要編譯自論文Participatory censorship and digital queer fand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ys’ Love culture in China)
參考文獻:
Gong, Y. (2017). Media reflexivity and taste: Chinese slash fans’ queering of European football.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0(1), 166–183.
Santos, K. (2020). Queer affective literacies: Examining “rotten” women’s literacies in Japan. Critical Arts, 34(5), 72–86.
Wang, Y. & Tan, J. (2023). Participatory censorship and digital queer fand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ys’ Love cultur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554–2572.
Ng, E., & Li, X. (2020). A queer “socialist brotherhood”: The Guardian Web series, boys’ love fandom, and the Chinese stat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4), 479–495.
West, S. M. (2018). Censored, suspended, shadowbanned: User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nt modera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4366–4383.
Wong, J., Lee, C., Long, V. K., Wu, D., & Jones, G. M. (2021). “Let’s go, Baby Forklift!”: Fandom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cuteness in China. Social Media + Society, 7(2), 1–18.
[Read mor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502-opinion-china-bl-fans-participatory-censo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