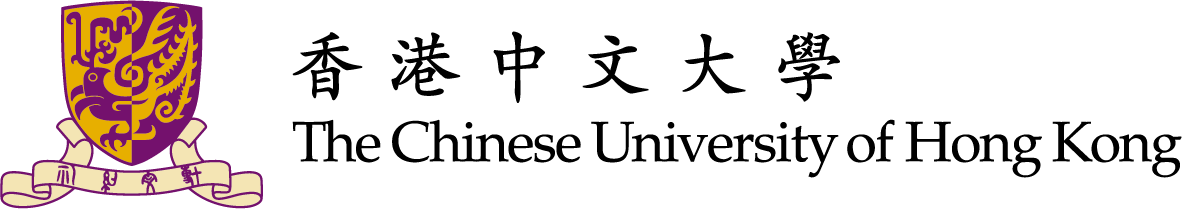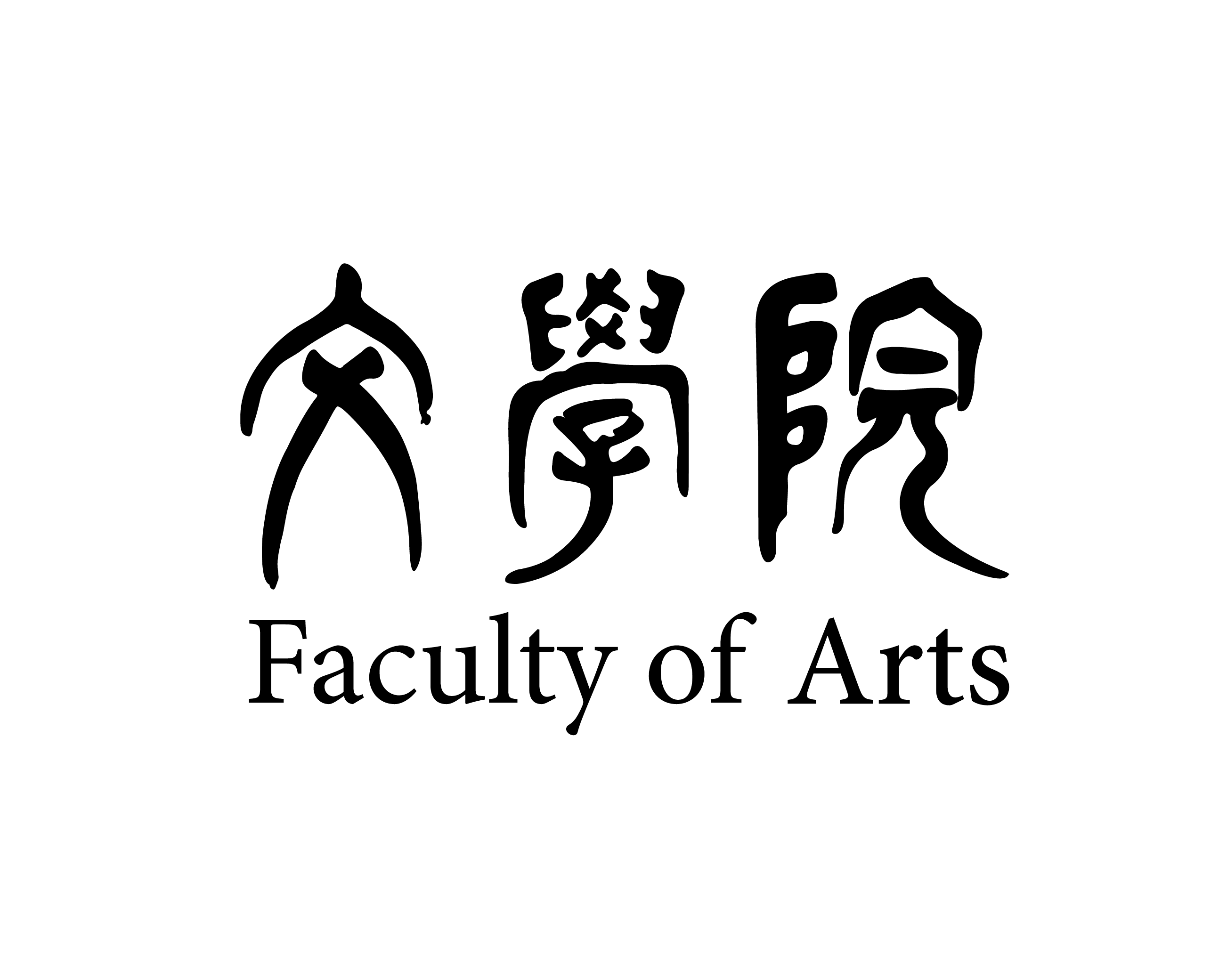Funding cuts, cancelled shows leave Hong Kong arts groups guessing about ‘red lines’ caused by national security law
[Prof. LIM Kok Wai Benny was interview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8 February 2024.] By Cannix Yau Hong…
Is the Boys’ Love genre paving the way for LGBTQ acceptance in Asia and beyond? Fans welcome recognition, but critics push for creative controls
[Dr. Ella LI Mei Ting was interview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29 December 2023.] By Lo Hoi-ying Hong…
A Dialogue between Current Leaders of Global Citizenship and the Future Global Citizens
Professor Kok Wai Benny LIM will be the speaker at an event--A Dialogue between Current Leaders of Global Citizenship and the…
Sign up to receive our weekly research email
Our selection of the week’s biggest research news and features sent directly to your inbox. Enter your email address, confirm you’re happy to receive our emails.
Prof. Song Hwee Lim on Taiwan Post-New Wave Cinema
Prof. Song Hwee Lim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to speak…
專訪學者彭麗君:長遠來看,我希望香港共同體不會消失
[Professor Pang Laikwan was interviewed by the Initium on 12 October 2020] 專訪學者彭麗君:長遠來看,我希望香港共同體不會消失 如果一切順利,9月6日,原本是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市民會早早出門排隊投票,建制派要用盡全力挽救選情,而在民主派與本土派之間,該有一番空前激烈的競爭。但《港區國安法》6月30日通過,當晚即生效。之後港府先後宣布大批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提名無效,並在7月31日宣布因 COVID-19 疫情選舉要延後1年。於是在9月6日這天,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獲得警方批准的九龍大遊行,訴求是反對政府押後選舉,以及關注涉嫌偷渡而在內地被捕的12名香港人的人身權利。 當日警方至少拘捕289人,包括一名新巴司機,他因懷疑向警察鳴笛而被截停。被捕時,司機臉上戴著一副豬嘴面罩,隔著巴士的茶色玻璃,粉紅色濾罐赫然可見。這是去年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最標配的裝備。司機隨後被捕,警方稱他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士巴拿」及「螺絲批」,並於9月10日以「不小心駕駛」罪名落案起訴。 「我感覺到警察的恐懼,明顯捉他不是因為士巴拿,是因為他駕駛著大巴士,又帶著個防毒面罩,他們最怕的可能是司機的那個面罩。」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彭麗君教授,並不認為民間的抗爭氣氛和運動動能被國安法打沉了,「可以說(運動現在)是被壓制了,但其實什麼時候、用什麼面目再出來也不知道。」 彭麗君教授的新書《民現:在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在今年5月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現在的副標題為譯者李祖喬博士由英文版的「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更換而來。書中分析的是雨傘運動的經驗,但李祖喬認為並沒有過時,「討論的還是一些關於民主、主權和文化等理論性的概念⋯⋯既是拒絕遺忘,又不是抱著事件不放,而是把運動產生的能量轉化成一些有待實現的視野。」…
Prof. Pang Laikwan on Gender/Democracy/Diversity: A Book Talk on Hong Kong Protest Culture
Prof. Pang Laikwan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Don’t Put A Ring On It: Why Modern Women Are Choosing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ver Marriage
[Professor Tan Jia was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Tatler on 16 June 2020] Don't Put A Ring On It: Why…
Prof. Katrien Jacobs on Gender/Democracy/Diversity: Pepe the Frog and Cuteness Activism Amongst Sinophone Youth
Prof. Katrien Jacobs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 李薇婷
【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文//李薇婷 時間:2020年6月2日 彭:彭麗君/譚:譚以諾/張:張可森/梁:梁寶山/李:李祖喬 整理、記錄:李薇婷 紀錄按:問答環節以私隱為由,以聽眾A、B、C的方法紀錄提問者。 政治現場與政治理想:阿倫特作為方法 彭:這本書的理論部份主要和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對話。身為一位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的學者,阿倫特是個有趣的人。她首先是德國猶太裔思想家華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好朋友和研究者。同樣是猶太裔的思想家,本雅明最後死在德國,但阿倫特成功逃離,若不是她,本雅明不會在五十年代後為全球思想界所熟悉。而阿倫特在離開德國遊歷於不同地方,之前之後也一直問:所謂「德國人」、「猶太人」,究竟是怎樣的群體。另一方面,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組成者大部份是德國猶太裔的離散學者,但在這群思想家當中,背負這許多種族、學術背景的阿倫特,卻與他們的思路明顯不同。再者,她雖是女性,卻從不願意被標籤為女性主義者,甚至於八十年代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她研究的許多題目均沒有從體諒女性的視角出發。但到了最後,儘管她背負的是整個德國哲學的傳統,總是從古希臘尋找資源來談論各種問題,但是,她卻不認同哲學家的身份,走進政治研究。凡此種種,加上她雖然經歷猶太苦難卻拒絕作猶太人的代言,再回過頭來提問,究竟整個歐洲哲學傳統背負怎樣的問題,她甚至認為納粹主義的生成必須從西歐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發展而理解,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她對此的反省態度非常強烈,甚至對猶太人本身的批評亦極為深刻。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吸引的,她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同時亦很貼地般提問政治是什麼、「參與式民主」為何、人如何作政治參與和日常實踐。我認為思考這些問題都能幫助我們離開現時的困頓。…
Art Criticism for the People (Talk organized by AAA , IATC HK)
Art Criticism for the People (Talk organized by Asia Art Archive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Hong Kong) This…
當漢娜.鄂蘭降落金鐘:國安法通過後,從哲學視角回首香港民主運動──《民現》 | 何明修
當漢娜.鄂蘭降落金鐘:國安法通過後,從哲學視角回首香港民主運動──《民現》 文//何明修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按:臺灣譯為「漢娜.鄂蘭」)是迷人的政治思想家,她親身經歷了納粹極權主義興起,被迫流亡海外,在黑暗的時代思索何種政治行動才能帶來人類自由。阿倫特從古希臘的城邦歷史得到靈感,入世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是比孤獨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更為可貴,也更能彰顯人類存在的特性。古希臘人將參與政治視為自由公民最高尚的義務與責任,基於這個理由,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中的「行動」(action),是優先於創造產品的「工作」(work)與純粹維持生存的勞動(labor)。 政治行動就是面對一群平等的同儕,參與者揭露自己的意圖,用言語交談取得共識、達成共同的決定,並且一同承擔其可能導致的後果。阿倫特堅持,政治只能處理公共領域的議題,包括當代所謂的身份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都不應介入。她擔心政治權力的擴張,試圖解決種族或階級不平等其所謂的「社會問題」(social question),將會帶來重大的災難,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即是如此。阿倫特所贊許的「革命」是古典意義下的「回到原點」,而不是帶領社會向前突破的大邁進。在她看來,美國革命是成功的,因為美國人起義是意圖恢復原先的自由,反對英國政府任意施加殖民地的苛稅雜稅,從而創造了新的政治秩序。 阿倫特的觀點很難用進步/保守、左/右等標籤來定位,但是可以確定的,她的政治哲學影響深遠。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政治學開始追求自然科學般的精準、選舉成為一套操弄人心的管理技術、權力越來越來淪為強制力,甚至是赤裸裸的暴力,阿倫特從人類處境來重新定義何謂政治。人類必得要參與政治生活,因為我們需要共同體相互扶持;但是也由於人類的有限性與創造性,我們打造出來的共同體有可能實現每個人的自由,也可能成為囚禁每個人的監獄。 晚近以來,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各地出現大規模的佔領運動與各種反政府抗議,也促成了許多學術研究著作的誔生。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2020 年 5 月)很可能是第一本有系統運用阿倫特的哲學觀點之著作。這本書是改寫於先前的英文專書,原書探討 2014 年雨傘運動以及之後的香港政治議題,隨著 2019 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中文版也增加了更晚近的反思。中國政府在6月30日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一國兩制提前宣告中止,在這項鉅變的脈絡下,閱讀《民現》一書具有格外深刻的意義。…
我們與愛的距離──英雄救美、愛情幻覺與《幻愛》的政治性| 林松輝
我們與愛的距離──英雄救美、愛情幻覺與《幻愛》的政治性 文//林松輝 且容我單刀直入:不論《幻愛》(周冠威導,2019)在鏡頭運用、構圖、色調等技術層面把屯門拍得再朦朧唯美,在處理男主角思覺失調時真實與虛幻不分的情節再清晰準確,都掩飾不了它在敘事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老土」。 光是片末男女主角冒着大雨互訪,繼而在人行隧道裡奔跑向彼此擁吻,無論此畫面是虛是實,都恍若1960、70年代改編瓊瑤小說的台灣愛情文藝片借屍還魂,只差沒配上一首時下等同鄧麗君的歌曲為觀眾催淚。 從敘事上來說,《幻愛》全然不脫英雄救美的俗套。起先是女主角葉嵐以輔導員兼研究者的身份接觸並嘗試幫助男主角李志樂,兩人墜入情網後需要被拯救的卻變成了女主角,因為她的「原罪」(性經驗豐富)顯然比患有思覺失調更「嚴重」和不可饒恕。女主角含淚告白她的「罪愆」的那場戲,即典型的無助少女(damsel in distress)的套路;而在她門外守候一夜的男主角,向女主角一再保證他「不介意」而贏取芳心後,兩人唯一的一場床戲,自稱沒有性經驗的男主角起先還神情緊張地背躺着,讓女主角為他除下褲子並叫他放心放鬆,但幾個柔和照明下的淺焦鏡頭快速剪接後,男主角卻忽然竅門大開般,將女主角壓在底下任他插入──是的,「老土」的電影不都是這麼拍的嗎?怎麼可能讓更有經驗的女主角主導性愛過程,甚至騎在男主角這個英雄身上,對吧? 片名《幻愛》應是直指男主角在幻覺中愛戀的對象,但影片可一點也沒有懷疑愛情本身可能就是幻覺,反而鞏固了「真愛能克服一切障礙」的迷思。其實,電影情節曾經暗示愛情是有「身價」的:男主角因為自己的隱疾而覺得「配不上」女主角,女主角則因為自己習於用性來交換利益而自認齷齪。但沒關係,愛情片自身的邏輯就是一種宇宙目的論(teleology),不管路途再荊棘滿佈,最後都會抵達真愛的終點。說真的,為了真愛,你可以去到幾盡?女主角為愛而放棄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的夢想,男主角呢?哦,原來英雄的宿命就是坐享其成,只要大方包容女性的「污點」,讓她付出救贖的代價,英雄就能抱得美人歸,而美人也就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從此為了真愛而堅貞不渝。 《幻愛》起先得到的好評如潮,讓人意識到原來我們與愛的距離這麼近。身為電影觀眾,我們如此渴望圓滿的結局,如此期盼有情人終成眷屬,以致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但這個「我們」是誰呢,有沒有性別、年齡、階級之分呢?此外,是不是所有的戀情,都「配得上」圓滿的結局,還是如近日所傳,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針對影視產業頒布的「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的禁令那樣,同性戀關係只能「點到為止,可轉為友情」? 和《幻愛》同屬一家電影公司發行、講述老年男同志戀情的《叔.叔》(楊曜愷導,2019),正面的影評大多讚許其細膩表現(負面的影評就不講了),但片子依然迴避了圓滿的結局,大概也契合此類戀情在現實生活中的結果吧(畢竟影片的製作前期參考了學者江紹祺的研究與著作《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蔡明亮1994年的《愛情萬歲》,片名更是故意的反諷,大膽提出愛情是不可企及的幻覺。回到《幻愛》,就意識形態而言,此片的愛情一點都不虛幻;反之,為了成就愛情,影片的敘事不惜讓女主角內化父權主義(如女主角的“uncle”)佔盡便宜卻污名化女性性權的迂腐觀念,不惜再度搬演英雄救美的陳舊戲碼。如陳穎指出,「《幻愛》所認同和成全的,是李志樂對愛情的想像,而這原不是葉嵐對愛情的想像」。 這種(從男主角的角度是)真愛無敵的邏輯,就可以繞過一切反思和批判嗎? 電影批評的路向眾多。根據學者達德利.安德魯(Dudley Andrew)的梳理,電影研究和評論的取向,從影迷鑑賞式的「石器時代」(約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經歷1970年代理論高潮(包含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的「帝國時代」,二十世紀末的「當下時代」則以文化研究為大宗。 文化研究向來着眼於權力、體制與身份之間的三角關係,尤其是這關係如何展現在被壓抑的弱勢族群身上;文化研究往往以意識形態為切入點,因為意識形態恰恰是以「一般見識」(common sense)的面目行走江湖,讓人們無視它賴以存活的權力與體制,彷彿「現狀」(status quo)即是真理,而不是權力透過體制長久實施與貫徹在個人與群體身上的結果。電影和流行文化之所以受到文化研究的關注,因為電影不只是電影;電影不僅僅是現實生活或虛構情節的再現,它更具有形塑身份的能力,包含個人與群體如何建構自我身份以及被他人界定與認可身份。《幻愛》後來受到一些批評,正是因為電影敘事中的厭女情結折射出的不但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更是對此「一般見識」的無感乃至否認,以致有些人看不到問題的存在便慨然宣稱沒有存在問題。 若有人認為從性別的視角對《幻愛》的批評,反映的是「『知識份子』的自大與離地」,甚至這種批評會「限制香港電影的發展」, 我們不妨詰問,在「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的社會氛圍之下(這裡的「我們」和「我哋」又是誰?), 甚麼人還有發聲的權利,是不是真愛無敵(好撚鍾意)就可以無視英雄救美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與性別幻覺。…
香港的時代證言:紀錄集體的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民現》 | 黃涵榆
香港的時代證言:紀錄集體的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民現》 文// 黃涵榆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當我在六月初從網路社群媒體得知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文後引為《民現》)的出版訊息(原為英文著作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我在知識和情感的層次上都受到頗大的震撼。 雨傘運動在形式上可計算的時間似乎已經結束,但是它所傳達的訊息、激發的追求民主的慾望和動力、對於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衝擊和啟發,都朝向未來開放,是進行中的、是將臨的。 做為一個研究過安那其和佔領運動的學術工作者和關心香港民主抗爭的台灣人,我對於彭麗君教授能有勇氣書寫這樣的一場運動或是尚在進行中的歷史過程感到相當佩服。我等不及台灣通路鋪貨之前,就立刻透過網路向手民主版社訂購這本書,也因此和主編譚以諾結緣,能有機會和讀者們分享一些想法。 《民現》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我其實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將雨傘運動放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全球一連串佔領(或「起義」)行動的脈絡之中,這些行動在起源、動員方式、訴求與目標等面向各具殊異性,共同點在於個體進行集體抗爭,催生政治行動的共同體。 第二部更貼近雨傘運動本身,探討與運動相關社交媒體、藝術創作、紀錄片和影像生產。第三部則回到普遍化的理論高度,從都市權、自由與其規限、法治等角度反思雨傘運動及其後的反逃犯條例(在台灣通稱「反送中」)抗爭。…